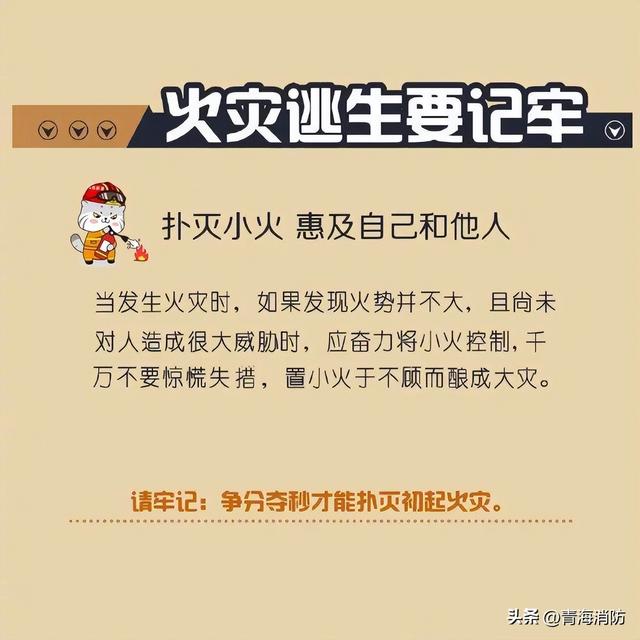抗战雪峰山战役纪录片(全景展示禹王山抗日阻击战的长篇纪实燃烧的禹王山出版访作者)
抗战雪峰山战役纪录片(全景展示禹王山抗日阻击战的长篇纪实燃烧的禹王山出版访作者)在二十多天的台儿庄保卫战中,六十军有一万三千多名官兵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另有五千多人伤残。一位古稀老人在回忆中说:“那年热天,禹王山上下大雨,一个个头颅骨随着山洪从山涧沟里淌到河叉,白花花一片,那是滇军留下的。他们大都是还未成亲的年幼人哟。”另一位老者的讲述更让人潸然泪下:“许多年以后,禹王山上还有磷火跳跃,那是滇军的魂;一到秋冬季节山风鸣鸣作响,就象阵亡的滇军在哭泣。一个秋雨连绵的傍晚,有人还见过一个阴魂附身的老妇人,哭喊着要回云南老家哩!……”禹王山,位居大运河东岸,台儿庄东南二十里。此山海拔虽然只有120多米,但它西连望母山,东接胜阳山、青冈山、锅山、胡山等,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对于遭受重大损失和善于山地作战的滇军而言,这块福地无疑是他们的“诺亚方舟”。从4月26日晚占领禹王山,至5月16交防,六十军官兵与敌军的机械化部队,进行了上百次的殊死搏杀。山头四次夺旗,敌军屡屡败退。禹王山防线始

文学创作,是一种责任与担当
2015年11月,一部反映徐州会战台儿庄保卫战的长篇纪实文学《燃烧的禹王山》,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
不久前的一个上午,朔风吹去了雾霾,冬日的阳光散发着浓浓的暖意。在邳州市区一家恬静的小院里,我们见到了该书的作者、省作家协会会员高福岗。几句寒暄之后,高福岗便开门见山:“古往今来,文学一直充满着一种强大的矫正力量;它不仅关乎着娱乐和趣味,也关乎着良知、关乎着是非,关乎着人心、世道。这样,文学便有了一种责任和担当。”说这番话时,高福岗的表情显得深沉而又严肃。
采风引发的创作冲动
2013年7月,已从某行政机关退居二线的高福岗,正在修改、打磨着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洪廊湾》。为了寻觅邳北地区的风土人情,丰富作品的故事情节。他来到了禹王山下采风。在村头路边的树荫下,许多古稀老人谈传说讲故事。但话题最多的却是七十多年前发滇军在这里打鬼子的场景。
1938年4月中旬,在台儿庄大战中溃败峄枣地区的日军,依然没有放弃“突破台儿庄、控制陇海线,占领徐州城”的既定目标。日军华北方面军集结了坂垣的第五和矶谷的第十两个师团,卷土重来,并以台儿庄以东地区为突破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精心构筑的三百里防线,岌岌可危。危难之时,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十军(滇军)奉命驰援。
滇军三万五千余名将士,根据李宗仁的命令,于4月22日早晨进驻台儿庄以东防线。这里一马平川,属于邳州邢家楼、戴庄范围。作为先头部队的183师杨宏光旅尹国华营来到集结地点立足未稳,甚至马背上重机枪还没有卸下,就遭到了日军坦克、大炮的突然袭击。尹国华营的五百余官兵只有一人活着,其余全部阵亡。几天后,军长卢汉和184师长张冲面对部队遭受的重大伤亡,毅然决定南撤运河岸,占领禹王山!从此,拉开了台儿庄保卫战的序幕。
禹王山,位居大运河东岸,台儿庄东南二十里。此山海拔虽然只有120多米,但它西连望母山,东接胜阳山、青冈山、锅山、胡山等,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对于遭受重大损失和善于山地作战的滇军而言,这块福地无疑是他们的“诺亚方舟”。从4月26日晚占领禹王山,至5月16交防,六十军官兵与敌军的机械化部队,进行了上百次的殊死搏杀。山头四次夺旗,敌军屡屡败退。禹王山防线始终固若金汤。
在二十多天的台儿庄保卫战中,六十军有一万三千多名官兵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另有五千多人伤残。一位古稀老人在回忆中说:“那年热天,禹王山上下大雨,一个个头颅骨随着山洪从山涧沟里淌到河叉,白花花一片,那是滇军留下的。他们大都是还未成亲的年幼人哟。”另一位老者的讲述更让人潸然泪下:“许多年以后,禹王山上还有磷火跳跃,那是滇军的魂;一到秋冬季节山风鸣鸣作响,就象阵亡的滇军在哭泣。一个秋雨连绵的傍晚,有人还见过一个阴魂附身的老妇人,哭喊着要回云南老家哩!……”
从禹王山采风归来,高福岗的心境一时无法平拟下来:六十军不远万里来到邳地,驰援台儿庄,全军将士经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然而,他们的牺牲与付出却由于台儿庄大捷的掩饰和后来的种种因由,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本土作家,他感到有义务,有责任,为六十军生死抗敌、抵御辱的民族精神树碑立传,以实现文学的教化作用。于是,高福岗暂时停止了长篇小说《洪廊湾》的修改,全身心地投入了长篇纪实文学《燃烧的禹王山》的创作中。
用史实还原那段尘封的历史
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文学爱好和创作激情,高福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曾创作发表了许多颇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中短篇报告文学,《神追大禹》、《光明的使者》、《老栗头和那眼古井》、《古栗魂》等,一经发表均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其中《伯父和他的两棵大榆树》在一次征文中,从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特等奖。而中篇报告文学《黄老出山》还获得了国家级大奖。2002年,他开始小说的创作,中篇小说《红坟》见诸于报端后,受到读者的热捧。2007年12月又出版长篇小说《樱花开了》,并被北京某影视制作方改编成了电影文学剧本。
“比起写散文、写论文,写小说是一道难题,比起写短篇、写中篇,写长篇更是难上加难!而长篇纪实文学要比长篇小说的创作还有不同的要求。因为长篇纪实文学不仅要展示内容的大气象、艺术的大营造,而且还要严格尊重史实,还要受到人物、时间、地域的限制。”高福岗深有感触:“但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长篇纪实文学,都要具备一定的密度、厚度和容量,都要把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讲给读者!”
“要把禹王山抗日阻击战抗击敌军的恢弘场景展现给世人,要把六十军将士生死御敌的动人故事讲给读者,不占有足够的历史史料,是寸步难行的。”在此后的三个多月里,他阅读了360多万字的参考资料:包括国内近年来对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战的研究成果,也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传记和回忆录;还有他不辞辛劳从云南、北京、南京、台儿庄等地有关单位和六十军亲属那里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拓展整部作品的历史空间和故事情节打开了广阔的视野。
“创作《燃烧的禹王山》这部作品,似乎也是在指挥一场战役,有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各方面的访谈,似乎就有了千军万马、刀枪剑戟,似乎就构筑了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有利阵地。”谈到这里,高福岗兴奋异常,拂去历史的尘埃,他说他已经清晰地透视到六十军在抗战前后复杂而又辉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包括部队的组建,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影响,还有与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队的情仇恩怨,以及痛击日寇的泣血场景。
有了六十军禹王山阵地生死抗敌、军长卢汉与长官部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纠葛以及共产党地方组织全力组织民众踊跃支前这三条主线,高福岗在整个作品作品中,便将散落一地的动人故事,象捡拾珍珠一般贯穿起来。其中有六十军在战斗中的真实故事,如陈钟书旅1084团第一连连长赵克于二十四日阵亡之后,他的哥哥赵继昌便将弟弟的骨灰装在干粮袋里,时刻背在身上,每逢与敌激战之时,便大声呼喊:“小鬼子,还我弟弟性命!”还有通信兵将计就计利用白族语言,让窃听的敌军连连失利等。也有根据六十军官兵克敌取胜的心理特征所艺术加工的故事,如军长卢汉在徐家洼指挥部按照老家云南昭通风俗,在大门上“挂符驱鬼”,面对禹王山阵地惨烈的战斗而“跪地拜山”、182师师长安恩溥的“禹王托梦”、184师师长张冲在禹王山山头上“布阵夺旗”和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员顾月明千里迢迢来禹王山慰问并“山头祭夫”等;都为作品增添了特殊的感染力,达到了“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和密集的思想”的艺术效果。
社会各界对作品的反响
“战争,不是作者的诗篇;而是将士们的浴血与眼泪。在创作完这部作品尾声的最后一句话时,我的心情却异常地沉重起来:就是再用百倍的努力,也不可能全面、客观地描述出当年抗日将士们金戈铁、气吞万里如虎的民族气概。《燃烧的禹王山》只是与六十军官兵一次晤面而已,但愿我的每个文字能够穿越时空。”高福岗如是说。
然而,长篇纪实文学《燃烧的禹王山》在禹王山抗战遗址被国家列入抗日纪念园之际一经面世,便收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衡说:“《燃烧的禹王山》,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记述了徐州会战中滇军(60军)卢汉部血战禹王山的英勇事迹……,本书史料丰富,史实准确。”
作为六十军军长卢汉之女的卢国梅女士,在阅读此书之后,也不禁感言:“在徐州会战中,滇军英勇抗敌的事迹震惊中外,但与战区长官部的内部矛盾、情仇恩怨却鲜为人知,作者能够客观地还原那段历史,难能可贵、感人至深。”
至于长篇纪实文学《燃烧的禹王山》出版发行的意义,中国一级作家,徐州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建有这样一句话:“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永远与它给广大读者留下的思考和所提供的精神营养有关。但愿《燃烧的禹王山》能给后世的人们以更多的战争真相揭示、更多的战争人物揭秘、更多的文学密码揭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