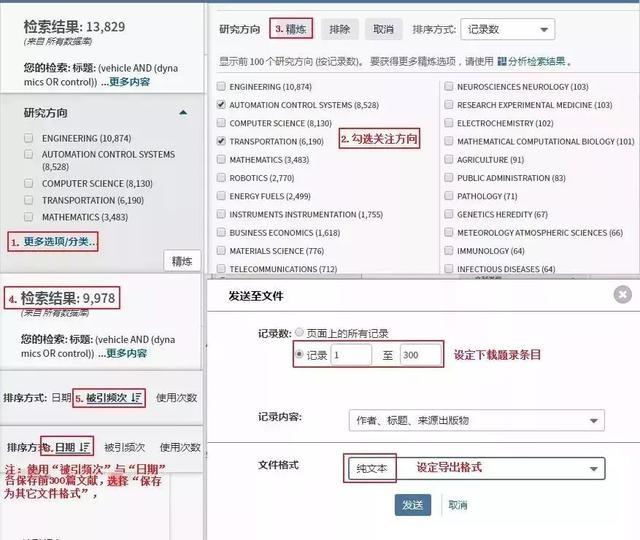尹氏儿女今何在(尹月武士的女儿)
尹氏儿女今何在(尹月武士的女儿)1870年,北海道开拓史次官黑田清隆访美考察后,为美国女性的学识教养所折服,回国后即向明治政府建议将年轻日本女性送出国门接受教育。此时,欧化风潮刮遍日本,岩仓具视恰好在组建前往欧美考察的使节团,出使目的之一是修订幕府时期与西欧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之二则是“亲眼观察欧亚各洲最开化昌盛之国体的各项法律规章等是否适于实际事务之处理,探索公法中适宜之良法,以便在我国国民中付诸实施”。使节团原本就拟安排留学生随行,“亲眼观察”并学习“制度法律”“理财会计”和“教育”(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明治维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318页),因此欣然同意黑田的建议,招募了几名女生。当时分别只有十一岁、十岁和六岁的山川舍松(1860-1919)、永井繁子(1862-1928)与津田梅子(1864-1929),就此在命运之手的推动下踏上了留洋征程(另两个女孩因健康状况不佳和思乡等原因早早回国

《武士的女儿:穿越东西方的旅行》,贾尼斯·P.二村著,马霖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月出版,332页,48.00元
1871年12月23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率领由四十八名政府要员组成的岩仓使节团和五十余名留学生,搭乘“亚美利加号”美国商船,从横滨起航前往美国。留学生中有五名稚龄女性,她们均出身于开明欧化的武士家庭,父兄中不乏出国留洋者,因此在明治政府的招募下应征,送年幼的女儿远赴异乡,她们从此背负上学习西式文明礼仪、日后为日本现代化发展效力的使命。
美国作家、学者和书评人贾尼斯·P.二村(Janice P. Nimura)的《武士的女儿:穿越东西方的旅行》(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本书出版于2015年,当年入选《纽约时报》年度“一百本值得关注的书”榜单,并于今年1月译成中文。这本书通过大量书信和日记等材料,完整还原了日本第一批女留学生的生涯经历。
虽然这几名小留学生出发时还懵懵懂懂,但已被家人和政府寄予厚望。父兄盼望她们回国后“习惯了美国人的做事方式,再讲一口流利的英文”(41页),既为国家前途尽力,又为家族争光。而明治天皇更是在岩仓使节团启程前发表讲话称:“我国女性不应该对关系到生活康乐的重大原则如此无知。虽然我们正致力于设计发展一套针对民众的文明开化体系,但是,对后代教育起到早期培养关键作用的依旧是母亲的教育!”(49页)一举将派遣女性出国留学之举提升到推进日本文明开化的高度。
因此,这几名女留学生似乎注定要拥有不平凡的人生。她们或许将在政坛大展宏图,运用出众的语言和外交技巧斡旋于日本和欧美国家之间,又或许能成长为杰出学者,将先进知识回馈祖国。总之,她们的人生陡然间被赋予了无限可能。同时,作为一名对大清留美幼童的辉煌事迹耳熟能详的中国读者,我期待读到一段激动人心的女性奋斗史。
然而,通读全书后,我却惊讶地发现,除了津田梅子,其他几名女留学生的命运似乎并未发生巨变,她们的人生轨迹因赴美留学稍有曲折后,便继续遵循常规向前平滑延伸,与日本同龄女性近乎平行地进入结婚生子、操持家务的既定轨道。而梅子尽管终身未婚,且在教育办学领域成就卓越,但从下文将进行的介绍和分析来看,她从未彻底摆脱“女性的天职是贤妻良母”这一传统思维的约束,乃至在教授学生时反复灌输这套显得陈旧,并且显然与其自身经历南辕北辙的价值观。为何这几位率先“开眼向洋”的女性未能挣脱时代和观念的桎梏?这要从明治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决策说起。

日本预计将于2024年发行的新纸币,其中5000日元纸币上的是津田梅子。
启程:新旧世界的交融
1870年,北海道开拓史次官黑田清隆访美考察后,为美国女性的学识教养所折服,回国后即向明治政府建议将年轻日本女性送出国门接受教育。此时,欧化风潮刮遍日本,岩仓具视恰好在组建前往欧美考察的使节团,出使目的之一是修订幕府时期与西欧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之二则是“亲眼观察欧亚各洲最开化昌盛之国体的各项法律规章等是否适于实际事务之处理,探索公法中适宜之良法,以便在我国国民中付诸实施”。使节团原本就拟安排留学生随行,“亲眼观察”并学习“制度法律”“理财会计”和“教育”(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明治维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318页),因此欣然同意黑田的建议,招募了几名女生。当时分别只有十一岁、十岁和六岁的山川舍松(1860-1919)、永井繁子(1862-1928)与津田梅子(1864-1929),就此在命运之手的推动下踏上了留洋征程(另两个女孩因健康状况不佳和思乡等原因早早回国,此处不赘)。
岩仓使节团的第一项任务阻碍重重,没能顺利完成。至于第二项任务,日本文学和历史研究者唐纳德·基恩曾做出如下评论:“无论如何,这些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认识了西方,而这种认识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他们有幸观察了繁荣和乐观时期的西方各国,他们可以将这些知识——不论是先进的机器、政治或者仅仅是欧洲人待人接物的礼仪——应用于日本。从这个角度看,岩仓使节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天皇和全体日本人民将分享他们通过漫长航程带回的硕果。”(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36页)舍松、繁子和梅子的确对异国的风土人情大感兴趣,“她们并不思念自己的祖国同胞,而是沉浸在美国带给她们的新奇之中”(95页)。尽管日方官员和她们的亲属努力保持她们与日语和日本文化的接触,三名女生还是迅速表现出与母语的疏离。年龄最小的梅子抵美后六个月就将日语忘得干干净净,开始用英语给父母写信了。待重返故土后,不通日语还成为她们融入社会和求职谋生的一大障碍,这是后话。
为了提高几名女生的英语能力,并帮助其更快地适应美国生活,她们被分别送往不同的寄养家庭。时任日本驻华盛顿弁务公使的森有礼精心挑选寄养家庭,最终决定请纽黑文颇具威望的公理会牧师莱昂纳多·培根接收舍松。繁子和梅子也分别寄养在优裕的知识分子和牧师家庭。
培根牧师对女性是否应成为知识分子持保守态度,在他看来,“女性的最高目标不应该是去震惊知识分子界,而是经营好一个家庭。在寄给森有礼的女孩们的成长备忘录中,培根写道:‘我们希望她们掌握主持家政的知识,能够像美国女性一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女主人。……她们将不止于了解如何向佣人下命令,而是更懂得如何教导佣人完成工作’”。对此,“森有礼非常满意。这就是明治政府的改革者们所欣赏的女性应有的行事方式和态度。‘贤妻良母’,这个词后来成为明治时代的一个热词。为了向前发展,明治政府需要这样的女性。女性角色固然重要,但任其发挥能力的范围仅限于她的家庭内部”(111页)。值得一提的是,森有礼是当时日本鼓吹男女平权最积极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他主张改革婚姻制度,推行契约婚姻,还身体力行地在1875年2月6日举行了日本第一场西式婚礼,与妻子交换了写入夫妇平权等内容的契约书。森这样的人物尚且如此看待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明治政府对这批留洋女生的期许就更有限了。此外,三名女生都与寄养家庭发展出极为融洽的、延续终生的情谊,因此不难想见寄父母对她们性别观念的形成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一篇发表在高中校刊上的文章已经使舍松在性别观念上的保守性初露端倪。她写道,“日本传统胜过西方模式”,“在日本,我们告诉孩子要遵从长辈的教导,父母比子女聪明,他们的做法也永远是对的。”作者对此评论道:“舍松并没有发觉,英文比日文还流利且正在为大学入学考试拼命学习的情形,与自己所秉持的有关教育的想法颇为违和”(137页)。舍松学业优秀,不仅是高中班级里唯一一个进入大学深造的女生,几年后更成为亚洲首位拿到美国大学学位(瓦萨学院)的女性。她的性格刚强果断,口才极佳,很受同学欢迎,也是留美“三人组”当仁不让的领袖。然而,满身才华对舍松而言似乎并非资产,倒像是负担。追求事业,还是回归家庭?这对矛盾将贯穿舍松的一生。

女孩们拜见日本天皇当日。从左至右:上田悌子,永井繁子,山川舍松,津田梅子,吉益亮子。
回家:“贤妻良母”成终生宿命
明治政府规定女生们在美留学的期限为十年,繁子率先回到日本。她已经顺利拿到瓦萨学院的音乐学位,还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干脆响亮”的告别辞:“只有我国的女性和母亲都能够受教育,我的国家才会成为先进国;只要女性依旧在应该上学的十五至二十岁间早早嫁人,那么女性群体就永远不会得到教育机会”(148页)。然而,繁子本人却在回归故土之前便与同为赴美日本学生的瓜生外吉订婚了。二十岁结婚的繁子固然接受了相对完整的大学教育,但她的生活仍然迅速被婚姻和儿女所占据。繁子一生生育了六个子女,尽管她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东京音乐学校担任音乐教员长达二十年之久,但这份工作是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并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她后来甚至还因以四十一岁高龄怀上第七胎而被迫辞职。繁子在“三人组”中的履历最为苍白,也是背负家计负担最沉重的一个。
舍松和梅子也在其后相继重返日本。此时她们与故土已经相当隔膜,作者形容舍松“更像是一个正在考虑前往异教国家的传教士,而非即将返回故乡的日本女性”(159页)。两人很快发现,要在故乡谋生并不容易。不仅语言和生活习惯需要重新适应,而且当时欧化主义风潮减退,国粹主义再行抬头,英文、西方思维和礼仪不再被日本人视为重要技能,局势与十年前已经截然不同了。
急于找到教书或翻译工作的舍松和梅子前往拜访黑田清隆,当初正是黑田的一纸建议将她们送出国门。然而,双方的会面并不愉快:“舍松和梅子开始谈论严肃的问题,有关她们在日本的未来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梅子她们发现,没有人把她们的意见当真。”之后,梅子写道,“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大海里的一滴水”(185页)。黑田没能介绍工作,日语又已遗忘殆尽,而且,年满二十二岁的舍松很快意识到未婚女性在当时的日本社会遭人侧目,难以立足。在拒绝了几任求婚者后,她终于决定与四十岁的陆军大臣大山严结婚,曾经“崇拜未婚的独立女性”的舍松也向“贤妻良母”屈服了。她最重要的身份成为“大山夫人”,发挥才华的空间被局限在舞厅、慈善晚会和厨房里。
1891年夏天,梅子和培根牧师的女儿爱丽丝·培根合著的《日本女孩与妇女》出版。书中提议借助“留学归来的男性的力量,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影响”,提升日本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并“提升日本女性的智力、道德水平和与之匹配的家庭地位”(256-257页)。因为自身生活环境的幽闭,舍松并不赞同这本题献给自己的书中体现出的乐观精神。
1902年,1882级瓦萨毕业生举行二十年聚会。这时的舍松已育有四名子女,还需抚养丈夫前妻留下的四个女儿。她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至于我,我能说出什么让你们感兴趣的呢?一件事也没有。”“与你们的生活相比,我的生活何其平淡……你们会想听我讲自己为什么辞退了一个仆人吗?会想听我说如何又雇到了新仆人吗?或者我和某些军官吃晚饭,席间他们一直在谈论军队的事,或者我的小儿子成绩糟糕,我对他已经失去耐心了,或者因为天气太冷,我饲养的蚕状况不太好,又或者我的生活被各种社交活动填满,来自各种俱乐部和组织的邀请信一堆又一堆……”(300-301页)。
有意思的是,虽然时常对自己的生活透露出沮丧情绪,舍松对在女性解放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女性活动家始终持保留和批判态度。当以梅子的学生平冢雷鸟为首的日本妇女解放先驱创办杂志和社团,为女性权益大声疾呼时,舍松在写给爱丽丝的信中这样评论道:“她们没有学到外国教育的精华,却已丢失日本女性最宝贵的品格——优雅、忍耐、纪律、责任。也许是我落伍了,但在我看来,日本女性教育没有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307页)舍松不遗余力地支持梅子建校办学,但无法接受和认可女性运用所学,为男女平权抛头露面、奋力抗争。终其一生,舍松恪守贤良淑德、家庭至上的教条,将就读于瓦萨学院时的意气风发封存在遥远的过往时光中。
再来看梅子。她发誓终身不婚,也确实履行了诺言。但除了没有重蹈两位朋友的覆辙之外,她的性别观念与舍松并无明显区别。梅子同样对平冢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认为她是“自私的新一代女性中的一个”。她写道,“真正的事业需要以平和的方式开展,说到底,需要的还是东方人的方式”(307页)。尽管梅子曾在《日本邮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我们需要更有力的领导者为女性权益发声”(263页),却不愿见到女性站到领导者的位置上。在她看来,女性的“行为举止不要引人注意,不要显得超前”,“要时刻表现得温柔、顺从、有礼貌,就像过去的女性那样”(293页)。她还提醒新时代的进步女性,“我们一定不希望看到,女性的思想和视野逐渐开放的同时,她们对家庭生活的不满和焦躁却也随之逐渐增加,甚至忘记自己最神圣的义务是,即使牺牲自我也要维护家庭和睦”(278页)。
同时,作者还敏锐地指出,虽然梅子轻视两位朋友在婚姻中所受的束缚,更为她们不断催自己成婚而烦恼不已,“舍松却实实在在是梅子希望培育出的那种日本女性,是日本新女性的典范:知识水平与丈夫相当,是丈夫的好帮手、好伴侣,而非一味为丈夫做苦力,积极了解国际局势,参与慈善活动,为自己的国家教育出优秀的儿女”(259页)。梅子不断教导自己的学生要成为“受过教育的男性的好伴侣,能够对儿子们产生正面影响的好母亲”(同上),也即希望批量培养舍松的翻版。一言以蔽之,“梅子从未在自己的论述中提出,其他女性可能和自己一样放弃有丈夫孩子的生活,将全身心投入工作。梅子是其自我主张的矛盾体,她没有家庭,但是她的教育事业却以推崇女性追求家庭完美为基调”(279页)。
“向梅子寻求力量”
1902年3月,岩仓使节团中还在世的成员举行聚会,舍松、繁子和梅子是“聚会席上仅有的三位女性”,“还像当年一样,交谈由男士们主导;晚宴后是一系列演讲,‘我们几个女人只负责听和欣赏’”(297页)。此时舍松已是侯爵夫人,梅子则在两年前创办了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堪称日本首屈一指的教育家,繁子也是音乐学院的资深教员,但她们在男性成员眼中仍然不过是“船上的小宝贝”。这时距她们乘船出洋已过了整整三十年,日本的男女平权状况显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不过,舍松等三人深情地回顾了当年的种种情形,好像并未受到多少冒犯。书中还数次描写她们觐见明治天皇皇后的场景,这位美子皇后“被臣民们视为这个时代‘贤妻良母’的象征”(306页),更是舍松等三人至高的榜样。她们生长于视女子为丈夫附庸的日本,在当时尚十分保守的美国度过青春期,又返回男女平权状况不见起色的故土生活,似乎缺乏接触和实践先进女权思想的渠道。

津田塾大学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与舍松等三人身处同时代的日本女性早已挣脱了“贤妻良母”的枷锁。1884年,翻译家深间内基将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著《妇女的被奴役》(The Subjection of Women)第一、二章译成日语,以《男女同权论》为题出版,为当时已渐成风潮的女性解放运动助力。这场运动将中岛湘烟(1864-1901)、福田英子(1865-1927)和市川房枝(1893-1981)等女性活动家的名字载入史册。荻野吟子(1851-1913)于1885年获得医生执业资格,成为日本第一位女医生,从此日本女性的从业范围便不再局限于教师、翻译,或者护士。还有在1926年以《武士的女儿》为题出版英文著作的杉本钺子(1873-1950)——本书书名显然由此而来——她在丈夫去世后携两个女儿来到美国,凭借多部小说和纪实作品,成为当时著名的作家。这些女性并不曾在少年时代亲身沐浴欧风美雨,但她们对如何争取女性权益却拥有比舍松等三人更深刻清醒的认识,在行动上也更为积极果决。
在本书结尾,作者动情地写道,“津田塾大学的学生们有时称自己为‘梅子们’,每逢期末考试和重要的工作面试临近,许多学生都会来到校园里这片梅树成荫的静谧一角,向梅子寻求力量”(312页)。如今日本的男女平等状况仍然不容乐观,但女性所受到的限制和压迫毕竟已大为减少。津田塾大学的学生们能自由选择喜爱的专业,数学、计算机、工程学等学科的大门都向女生们敞开了。梅子、舍松和繁子若能见到这番景象,也当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