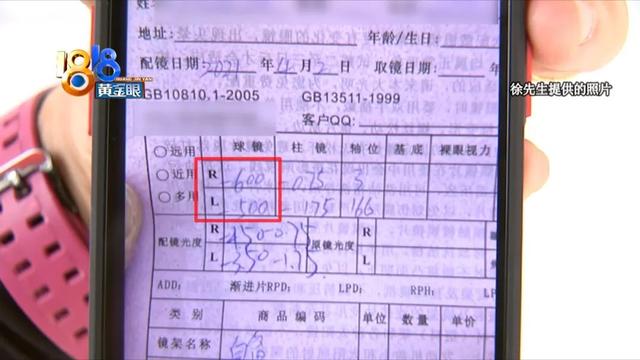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越简单越好(想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越简单越好(想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如这两种解释不能说不对,但也难免有片面之嫌。我们读一下《论语》便会发现,孔子在不同的时机面对不同的弟子,对于“仁”的阐述也是不同的。且孔子从未如许慎或是韩愈一样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一直在阐述身为“仁者”应当如何作为以及“仁道”是如何体现的。

什么是“仁”?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古今学者对其地解释有很多。
比如《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从二”。意思是当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要相亲相爱,这是一种广义的道德观念。
而自称继承儒家道统的唐代文人韩愈则认为“博爱之谓仁”。也就是所谓“仁”,就是人要爱戴每一个人。
这两种解释不能说不对,但也难免有片面之嫌。
我们读一下《论语》便会发现,孔子在不同的时机面对不同的弟子,对于“仁”的阐述也是不同的。
且孔子从未如许慎或是韩愈一样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一直在阐述身为“仁者”应当如何作为以及“仁道”是如何体现的。
如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等等。
这就说明孔子的“仁”绝非仅仅是“爱人”这样一个狭隘、单纯的道德观念,其背后应当是蕴含着很深厚的人文文化的。
想要了解这背后的深层文化,则一定要找到这种文化的根基。
要知道,我们中国古代思想与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代思想是截然相反的,西方人的思想是典型的“务虚”思想,而我们中国古人的思想是绝对的“务实”思想。
西方人否认眼见为实,他们好奇的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人意识的本源这些虚无缥缈跟现实生活没有太多联系的问题。
而我们中国古代思想诸如儒家、墨家、法家、杨朱学派等等思想流派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其实就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问题。
纵使道家学派的理论触碰到一些关于本体论的话题,最终也在“天道”的边缘急转直下,由“道”引出“德”,重新回归人文序列。
而古人所谓的学问,从小读的书、学习的知识,也都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最终也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中的人伦关系。
这种差别是怎么来的?
我们观察一下我们中国的地貌便会发现,中国大陆是属于一个封闭式地貌。
北部和西部是草原和荒漠,东部是大海,南部则是山区丛林,唯有今山东、河南一带拥有大片平原以及黄河冲积出的肥沃土壤。
所以,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上古时期,我们华夏族自然而然便定居在了中原这片土地,依托大河平原发展农业,这也就是华夏文明的开端。
而农业的发展就必须要涉及人与人的协作,人文文化就这样有了诞生的土壤。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古老的农业社会人口不断增加,但生产力却不足以打破中原地貌的封闭性,所以人文压力诞生,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人与人之间该如何相处这个问题,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人文文化就这样诞生了。
而西方为什么没有产生这种人文思想,因为欧洲地貌多山石,不利于大面积发展农业,且欧洲大陆西部沿海,中部还有一个狭长的地中海。
人们发展不了农业,为了生存便只好跨海去非洲或是中亚换取粮食。
人口的大量流动导致了欧洲并不会存在大量人口封闭在一个固定区域的情况,不存在人文压力,自然也就不去关注人文问题了。
归根结底,一个民族或是一片地域的人民所秉承的文化,是受到生存环境的影响而衍生出来的。
所以,人们常常说汉文化的同化力非常强大,历史上诸如鲜卑、契丹、蒙古等外部民族来到中原地区都会被汉化。
其实并不是因为汉文化本身具有独特的魅力,而是因为以人文精神为根基的汉文化是唯一能够与封闭的中原地区相适应的生存文化。
无论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文化,想要入土中原,都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在封闭地域间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人文压力,而此时汉文化就是解决这种压力的现成方案。
生存境遇促生了文化根基,文化根基发展到一定程度则自然要结出五彩斑斓的文化成果,就这样我们先祖文化的第一次开花结果便选在了那个热闹非凡的春秋战国,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百家争鸣时期。
而在这次文化大丰收中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正是最耀眼、最硕大的文化成果之一。
这就是“仁”文化的根基。
可能有人会质疑“仁”文化的成功性。
因为无论是孔子最初的“仁道”,还是后来孟子提出的“仁政”,亦或是后世诸如宋明时期理学家为复兴儒学提出的“天理”学说、阳明先生“良知”之学。
儒家的“仁”似乎始终不得推广,甚至一度出现乱象,而到了近代儒学道统更是被连根刨断。
其实“仁”文化的成功并不体现在表象上的推广,而是通过文化渗透为我们中华民族打下了坚实的信仰根基。
其实不论是许慎还是韩愈,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正统儒家的“仁”,在爱的体现上是有差别的,不是绝对大公无私的博爱。
要知道人类情感最根源处的爱来自血缘纽带,人面对跟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是不会天生就产生爱的,人类原始、根源处的爱只有对父母的爱。
这种感情是从动物感性中延伸过来的,这是动物的本能。
所以孟子讲:“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在儒家的观念中,人对父母的爱一定是高于兄弟的,而对兄弟的爱一定是高于朋友的,对朋友的爱则一定高于陌生人的。
比如孟子在与万章关于舜的讨论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为顺与父母,可以解忧。”
尧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舜,九个儿子也都听命于舜,还把国家财富、牛羊、粮仓、官吏全都交给舜。
如此威风舜依然很难过,因为他跟父母兄弟相处的不顺,父母和兄弟总想杀害他,他觉得自己最重要的情感无处安放,无法尽到孝悌之道。
这就可以看出古人对这种血亲情感的崇拜,血亲之间的爱是至高无上的,而对血亲之间的爱也绝对与对朋友甚至妻子的爱有所不同的。
这种有差别的血亲至上的爱才是真正的“仁”爱。
而诸如韩愈所谓“博爱之谓仁”,对所有的人都是同等的爱,则更多偏向于墨家的“博爱”学说。
尽管墨家也是人文根基衍生出的人文成果,但相比儒家的血缘纽带的爱,它并不顺应人的本性,它带有强迫性。
可尽管“仁”不是“博爱”,但“仁”之爱也绝不是只爱自己亲人的自私的爱。
儒家所提倡的“仁”爱是希望人们能够优先重视对父母、血亲之间的爱,再将这种情感向外推广、扩充,进一步爱妻子、爱朋友、爱陌生人最终爱天下百姓,由此来实现天下之大爱。
这是血亲情感在人伦压力下的升华,是利用血缘纽带实现社会稳定的伟大创举。
很显然,这个创举很成功,因为这种观念很成功地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血液中。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外国人称呼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往往都是先生或是女士,而我们中国人呢?
称呼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也作叔伯、阿姨、爷爷、奶奶,称呼同辈也都是哥哥、姐姐。
注意这种称呼是什么?
是血缘称呼,用血缘称呼来称呼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这就是血亲情感的推广与扩充,是“仁”的最直接体现,是我们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
而我们再读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也就是古人长大成人的必修课,其中八条目的次第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个人怎么去面对社会,要先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心性层面开始自修,把自己内心看明白、管理好了。
之后才可以接触别人,而接触别人要先从接触家人开始,把家庭关系处理好,也就是“齐家”。
要知道,古代的“家”可不是现代人学来西方的那种一男一女的两口小家,而是家族。
五世同堂或是六世同堂,子女成群,算上娶来的女方的家族,动辄一个“家”要几百号人。
想要处理好几百号家人的关系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
做到了“齐家”才能够去处理社会问题,最终“治国”、“平天下”。
所以“齐家”是一个人由自我心性修养到入世做事的过渡环节。
家庭关系是每个人都逃避不了的,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但其实祖先早就给我们支了招,欲齐其家先正其心,自己心都不正,家庭关系肯定处理不了,心怎么算正?
“仁”就是正。
把情感深处对父母、兄弟最原始、纯粹的爱翻出来,摆在第一位,少一些虚伪,真诚对待家人,把利益往后放一放。
做到了如此家庭关系自然也就能处理好了。
而之后把这种情感扩而充之去发向社会,自然也就能够做到善待他人,家、国、天下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一码事了。
用血缘纽带关联社会,用血亲之情稳定社会关系,这种顺应人性的治世哲学实在是高明。
所以,儒家“仁”的思想是人们在人文压力下对社会最顺应人性的拷问成果,是人类情感在人伦社会中最合理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是人与人之间生存元素高接触率下最有效的情感调和剂。
当代社会,全球人口暴增,而信息化技术将全人类连接在了一起,任何一个人的生存成本中注定绑定着别人。
这与上古时期华夏农业文明在封闭的中原地貌下因人口暴增而引发人文压力的情况十分相似,所以来自全人类的人文压力是我们必将面对的。
如此一来,我们积淀了千年的“仁”文化是否就是祖先提前为我们准备好的应对法宝呢?我们的“仁”文化是否应该重新被重视起来呢?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